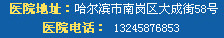“早先,俺刚出海打渔那会儿,驶的就是这样的帆船”,老船长刘元保指着展台上的一只帆船模型说。
日前,在巧手云集精品荟萃的青岛市首届乡村手艺大赛现场,这样两只船模,颇惹人注目。而其也为老刘赢得了这次大赛最高奖等,三个一等奖中的一个。
两条船,一条是帆船:三面赭红的帆,在挺立的桅杆上张扬开来,似乎可以听见海风在猎猎地吹。红松的龙骨,刺槐和柞木的骨材,全部是原木原色的舱板、船舷。从整体的帆船格局、构造,到最微小的船体部件,从船的姿态、气度到神韵,一切都如40多年前,刘元保刚刚出海打渔时那条帆船的模样。只不过,这是一条缩微版的帆船。按照18比1的比例,老刘将当年那条18米多的大船,雕琢制作成了一米大小的船模。
还有一条机动船:也是一米长,缩微比例同样为18比1。这艘船除甲板舱面保持原木颜色外,通体漆成了海蓝,船上设备如雷达天线,网具起吊装置,救生圈,双锚,等等一应俱全,船头升起鲜红国旗,船尾彩旗飞扬,令人叹服的是,就连桅杆下的传动构件、船尾底部的螺旋桨推进器,也都做得惟妙惟肖。可以想见,倘若放大成20米长的原版,驾驶着这样一条气宇轩昂的船,在开海后的万顷碧波上驰骋,该是多么激越和豪迈。
两条船模,静静地泊在展台上,接收着人们的围观和赞羡。它们的主人,也在一边平静地望着它们,就像望着自己的老朋友。
是呵,真的是亲到心里铁到家里的老朋友。那条帆船模的原型,就是当年17岁的刘元保,刚开始出海时,驶的第一条船。
刚上船,刘元保从水手学起,跟着船老大,船上的活计一样一样从头学起。古往今来,天底下哪一个学徒工不是吃尽千般辛苦,才能学到真本事?况且还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上。
浪水颠簸,风吹雨打,海雾潮湿,渔路迢遥,这些都是寻常的。出一趟海,寻常40多天在海上漂泊不能回家,这也寻常。赶着潮水,起早摸黑,披星戴月,活儿急起来不亚于陆地上的三夏“双抢”,若论起织网补网、炒菜做饭等等,诸此这般印象里应由心灵手巧的主妇们干的活儿,船上的水手却也是必须熟练掌握的技能。
崂山,自古也叫“劳”山么,人的秉性也随水土,所以崂山的汉子向来能耐得下劳累吃得下辛苦。敢驾着一叶小舟出海的崂山汉子,更是如此。
刘元保在这条帆船上干了三年。那时,船出海全看天,没风,不行;风向不对,也到不了中意的渔场。刘元保回忆,那时候,他们一般是在谷雨节气过后,借着风势,驶船往南方去,过江苏连云港,最远抵达长江口以北的公海,那里是传统的渔场。
帆船要看风使舵,逢上六级左右的风,刘元保他们的帆船能跟得上铁壳的大轮船。但风向、风力再怎么合适,帆船再快,跑到长江口附近,也得一天一宿。
刘元保他们去长江口渔场,主要是打鲅鱼、白鳞,还有鲐鲅。出去一趟,最长五六十天,不上岸不回家,那渔获怎么办?那是也没有冰块冷藏,打到的鱼就拿盐来腌。
那时候,甭管在哪里,吃饭还是大问题。百姓日子过得都还紧巴。出远海,刘元保他们带的干粮,也主要地瓜面的饼子、窝窝头。带点菜,出海不几天就吃没了,再说即便带多了也存不住。没有菜,下饭的就一样。啥?海里的鱼虾。
要说新鲜,那可真是新鲜。跟老刘聊起来,他现在还是对当年再船上吃的鱼赞叹不已,“真好吃”。可不,我也有过一段海岛生活的经历。在海上,刚打上来钓上来的鱼,根本不需要什么大厨,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料酒八角十三香,就搁海水里洗了,放锅里煮就行,那个鲜。所以,万事都有个辩证法在里面,苦与乐,遭罪享福,从来都是人生味道的两面,总是不分家的。当然,个中滋味,也只有个中人体会得最真切。
三年时间一晃而过。三年后,刘元保的渔船由帆船,换成了机帆船,就是又有帆,又有马达螺旋桨推进器的。最早是15马力的。年前后,又上了20马力的全机动船,航速能跑6到7节。再往后,船体越来越大,马力越来越足,60马力,80马力,直到每小时能跑11、12节的马力的铁壳大马力渔船。
师傅领进门,成才在个人。一点儿也不假。勤劳肯干,不惜力气,又用心,爱琢磨,有悟性,刘元保在当了三年帆船水手之后,就开始了他四十年的船长生涯。不是谁都能当起这个船老大的。能把准方向,懂潮水,会看天气,船上的伙计样样都能拎得起放得下,关键时候还要能扛起来顶起来,成为船上5、6个人的主心骨。这可不简单。但刘元保做到了。40年的海上生涯,他付出了多少辛劳,经历了多少风浪,扛起了多大担子,船上的水手伙计们知道,大海知道,船知道,刘元保自己也知道
在海上,刘元保驶着船,一直到60多岁。这个年纪,在办公室里成天坐着的,也该退休了。其实,如今的生活宽裕、富足,早已不再需要老刘跟当年那样打渔养家。他出海,更多是自己的习惯和喜好。家里孩子们也一次次劝他,于是老船长刘元保就不再驾船出海,跟自己的兄弟伙计们一样,回到岸上,在港东村家中享享清福。
四十多年来,长年累月地在海上颠簸,这回到岸上了,却又不爱老是在家歇着。瞅着好天气,潮流也合适,老刘就去海边钓钓鱼。回来后,甘冽的崂山山泉水,泡一壶崂山茶,悠然见海,见山,也见云。
不再出海的日子,就这么清和而闲适地过着,挺好。但身边的两个事儿,却让老船长又闲不住了。
一是有一次,十来岁的小孙子跟着他在海边玩,看见水面上飞快驶着的渔船,就问他:“爷爷,为什么船没有轮子,还跑得那么快呢?”
小孙子的问题把老刘逗乐了。于是,老船长就将渔船的螺旋桨推进器指给小孙子看,还一一将船体各部位的名称、构造以及功能作用讲给他听。
看小孙子听得认真,老刘也很高兴,不过高兴之余,也有些感慨:如今,村里的渔船比起当年盛时,是越来越少了。记得最多时,村里60、80马力的船,就有80多条,而现在只剩下不到十条了。
年轻人上学的上学,进城上班的上班,要不就是办渔家宴搞旅游,很少有愿意出海打渔的了。照这个趋势下去,村里的船还会逐渐减少的。将来,或许再有孩子问起小孙子曾经问过的问题,到码头边找条船指给他们看,怕是也不很容易呢。
再一个事儿,就是老刘的侄女结婚时,小两口想买一件船模当摆设。海边渔家人么,从小对船都有感情。可是俩人往即墨城里跑了两趟,也没看到有中意的船模。于是,老刘亲手做了一件,送给侄女,他们很是满意,说比即墨商店里卖的强多了。
就是这些事儿,让赋闲的老船长,开始了与他的船在岸上的又一次亲密之旅。于是,从年开始,老刘在钓鱼之余,添了一样新“工作”:造“船”,制作船模。
从驶船打渔的船老大,到制作船模的手艺人,60多岁的老刘这次“转型”,可实在是不简单。
一条20米的大船,需要多少材料、部件,一条一米长的缩微船模,就需要多少材料、部件。只不过,大船的制造,通常是在造船厂里,由好多个工种的专业工人,借助现代化的设备、机械、工具,通力协作,耗费大量的工时,才能成功下坞。
而在老刘这里,船厂就是他的家,工人只有一个,还非专业熟练工,而是半道自学琢磨的。至于专门的机械设备工具,老刘更是没有,他只有一把电钻,一架打磨机。
不可思议的是,就是拿着这把电钻,再借助打磨机,自学成才的退休船长刘元保,硬是在7年时间里,手工造出了十多条精美的船模!
把时间用在哪里,哪里就给你回报,这话不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而且从来都不负。
年轻时的刘元保,就爱钻研,做事上心、用心,不惜气力,而且关键是能坐得住耐得住。所以,才有可能仅仅在帆船上当了三年水手,就能学成本事,带着伙计们撑起一条船来,而且船老大一干就是40多年。
有这个精神头儿,有这股子劲儿,即便现在已经年纪大了,但一样能干出样名堂来。当然,事情总是想想容易,说说容易,真要动手做起来,却不像想的、说的那样。着着实实,要过几关的。
第一关,是船模的构造设计。机动船还好一些,因为,毕竟海边码头上就有实实在在的原型,泊在那里。无论是总体框架、构造布局、部件位置、尺寸大小、卯榫结合等等,哪样有些拿不准了,溜达到海边,看看就成了。
而最早的帆船,如今已经没有实体原型了。40多年的光阴淘洗,当初3年船上生活的映像,也都消磨得差不多了。
好在老刘是个有心人,尽管没有想到40多年后,自己会凭着记忆,缩微制作复原一条当年的帆船,但彼时朝朝暮暮与帆船守在一起,那条船在刘元保脑海里,就像一个兄弟、老友,无论是相貌、个头、秉性脾气,甚至是嗜好习惯小毛病,老刘都知根知底一清二楚。
所以啊,龙骨和骨材怎么选,怎么起框架,三面帆大桅、二桅、后梢怎么布好位置,棉线织成的篷布,怎样用猪血染色、用桐油刷漆,传动轴和桅杆的关节部件怎样咬合妥帖磨合顺畅,这些,都在老刘心里,明镜儿似的呢。还有,船材的选择,一定是红松、洋槐还有柞木,柳树和桑树,是不能用在船上的。我问老刘,是因为木材材质和谐音忌讳吗?老刘笑笑,说老辈上一直就这么传下来的。
人们常将好的手工艺人,称作能工巧匠。我想所谓匠字,其实是一个执字。如果没有一股子执著的心劲儿,如果不是近乎偏执痴迷的打心眼里的热爱,如果不是朝思暮想凝心聚力地执执以求、以研、以琢磨、以探究,世上哪里会有那么多轻轻巧巧的成功?!
这个年纪了,在海上辛劳了这么多年,也该好好歇歇了。制作船模,劳心费力的,图个啥呢?
问老刘,他笑笑:没啥,就是想给这些越来越少的船,留下点什么。
哦,我明白了。
我知道,也理解,生活中,就在我们身边,是有这样一些人,他们就是想做一些事情——这些事情,“不知者”觉得有些执,有些不可思议;但“知者”,却觉得有其价值和意义,而且这些价值和意义,也许一开始没觉咋的,但会随着时间的变迁慢慢显现出来。
而被“围观”、“旁议”的人呢?他才不会管这一些呢。觉得该做,觉得是“对”的事,做就是了,专注地,一心一意别无旁骛地,去做,才不会把时间,用在去解释上呢。
有这个工夫,“老船长”们还不如将其放在其念念如一的“宝贝船”上呢。而且,那“宝贝船”,它们瞅着“老船长”们,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呢。
而且,不仅是老船长和他的“宝贝船”相互知悦、欣赏,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,也有越来越多的人,喜欢、敬佩且羡慕他们呢。而这,也是我参观青岛市首届乡村手艺大赛之后,忍不住要为老刘和他的“宝贝船”写点东西的缘因。
一切过去,皆为序章。一切过去,也皆成记忆。于国家,为国家记忆;于城市和乡村,为城乡记忆;于个人和家庭,亦为百姓记忆。而于奋斗、梦想和探索,则是回望来路时的欣慰,抚摸往事的感慨,瞩目远方时的踏实和坚定。
感谢老船长刘元保,是他和他的“宝贝船”,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过去、关于沧海也关于人生的宝贵记忆。
这些宝贵的记忆,且让我们珍视之、感恩之,并从眼到心里,带着温暖的笑容,常温常新之。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hl/3059.html